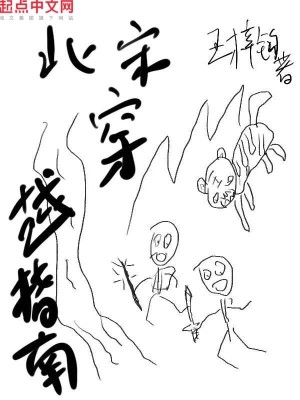小嗨书 > 《音乐家们的手指》by公子优 > 第77章(第3页)
第77章(第3页)
温月安递了一个枕头到床下,然后拿起床头的字,看了很久,光看还不够,他还将那字盖在自己的脸上,不停地闻那幅字的味道。
“……你……贺玉楼……”温月安嘴上这样喊着,可是心里还是在一遍又一遍地喊师哥,不知道喊了多少遍。他紧紧抓着被子,几乎要把被子抓破,“明天我们去哪个乡下?”
“老家应该有一块地,一座老屋。”贺玉楼说。
温月安又在心里喊了好多声师哥,才说:“我不去。”
床下静默许久,才听到贺玉楼问:“为什么?”
“……你……以后还……弹琴吗?”温月安问。
他等着贺玉楼的回答,有若一场酷刑。
窗外的明月被浓云掩去,寂静的屋中变得黑压压一片。
床下没有任何声音。
烫人的泪水从温月安的眼眶里滚出来,顺着眼角流到他的耳朵里:“我只想跟……手指……完好无损的……能弹琴的贺玉楼……一起。”
屋中仍旧一片死寂。
过了一会儿,似乎有细微的水滴声响起,床板有一点动静,又很快消失了。
“人活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温月安顿了片刻,颤声道,“我只想弹琴。”
浓云仍未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