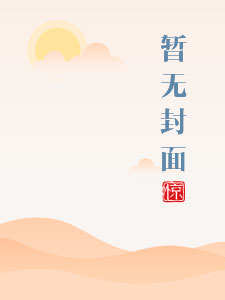小嗨书 > 【y24专用】【42】致小天使 作者:白日梦羊 > 第109章(第2页)
第109章(第2页)
塔季扬娜住在市区,两人约在她家见面,燕棠定了离得最近的一家商务酒店,这晚就近找餐厅吃了顿饭,捧着杯热茶在酒店房间里开始写立项策划书。
前期找章叙慈和玛莎这两位大编辑聊,只是碰了下可行性,在基金会系统里完成了立项登记,意味着各部门可以配合她进行一些初期工作。但项目真正开始,还得等策划书在基金会的项目管理组审核通过。
基金会这些年相当于在中俄文化市场当中间人,一边对接译者和作者,另一边整合出版社资源,内部对接效率很高,是个很不错的平台,但相应的是要求也非常高,如果看不到销路,点子说得再好听也没用。
燕棠列了几位要预先谈合作意向的作家,为首的就是塔季扬娜。
她之前那本译作《苦月亮》就是塔季扬娜写的,在国内销量很好,也给燕棠带来一笔可观的收益。如果她这次项目里包含的作家有国内的销售作品先例,策划书过会概率会高很多。
第二天下午,燕棠带着自己的译作、精心准备的小礼物和最新版本的策划书敲开了塔季扬娜的家门。
尽管她们已经通过邮件联络多次,这还是两人第一次见面。
塔季扬娜有棕红色的头发和碧蓝色的眼睛,不笑时有着斯拉夫人特有的严肃,一笑起来就变得很随和。
“Yana。”她和燕棠拥抱了一下,“你的样子和我想的一模一样。”
燕棠也笑了,“你也是,真高兴能和你见面。”
和作家打交道,尤其是和有个性的作家打交道,一定不能立刻谈正事,那显得太过功利。
燕棠在这上面吃过亏,和塔季扬娜坐下来后没有着急,而是跟她漫无目的地闲谈。
大概是早就通过文字神交,译者和作者之间有一种奇怪的共鸣感,两人迅速地熟稔起来。
从旅游见闻聊到文学作品,从俄罗斯历史聊到美学风格,又从咖啡和茶的口味聊到睡过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