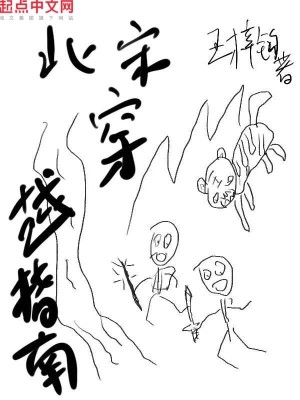小嗨书 > 《剑与她》作者:施黛 > 第208章(第2页)
第208章(第2页)
白婳:“安心什么??”
宁玦不咸不淡啧了声:“原本是想带你随我一道进京去,现?在看来,我实在是不放心。又是被高门?子弟觊觎,又是得太子殿下青睐,旧地有旧交,你在京歧认识的人这么?多,万一来个故地重逢,我心里可不痛快。”
白婳闻言只?将重点放在‘进京’二字上,眼?下兄长还在京城,对于旧地,她心中当然有牵挂。
“公子要进京去?何时??”
宁玦笑笑:“等解决完你的事?。”
白婳心头惴惴,有点不安,公子说话藏一半,含义不明,叫人琢磨不透。
两人相隔一月有余才见面,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她全然不知,心里当然没找落。
白婳暗自腹诽,或许她近日在季陵的经?历,丝毫逃不过公子的耳目,而公子的行迹,她却全无所知,真是不公平。
她心中抱怨,面上表情自然也带上情绪,嘴角不自觉向下垮下去。
宁玦看着?她,再次搭话问:“想不想跟我同去?”
白婳负气说:“想不想的哪由?我说了算?如今公子什么?事?都不同我说了,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若公子对我心生防备,怕我再度背叛泄密,不如趁早离我远点,省得操这份心,觉都睡不安宁。”
“你心中若真怀疑我对你设防,恐怕嘴上根本不会这般坦然地跟我抱怨,有恃无恐,有个词是叫这个吧?”
心思被宁玦看穿,白婳面上微窘,耳尖热起来,一时?说不出来辩解的话。
她不想与他?继续聊了,可宁玦却没有要停的意思,盯着?她,好整以暇道:“一月不见,脾气倒是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