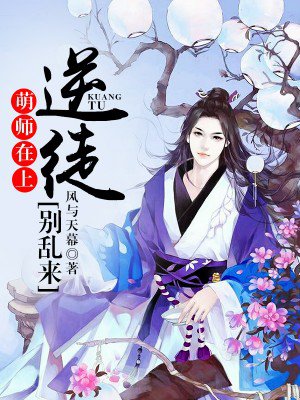小嗨书 > 或许春天知道 > 第135章(第1页)
第135章(第1页)
直到把氧气耗尽,孟镜年直接将她打横抱起,径直往浴室走去。
浴室通风整天,干爽洁净。
而没过多久,便变得雾气腾腾。
林檎后背靠在那平日一点水渍都没有的白色瓷砖,冰块似的凉津津的一片。
垂眼,看见孟镜年墨色柔软的头发,淋湿了往下滴水,他正垂眸,耐心而温柔地照顾昨晚被他咬破的地方。
痒与钝痛,不知道哪个更强烈。
来不及擦干,孟镜年穿上灰色浴袍,展开一张干净浴巾,将她裹起来,就这样抱着去了卧室。
下午的时候,窗户打开通风忘了关。
夜里起了风,吹得白色纱帘掀起一角,又轻轻地扑在玻璃上。
林檎额头用力地抵在枕头上。
转脸看见床头柜上岩石星球的扩香石、铜色金属灯罩的落地灯,以及那棵漂亮的金山棕……
目之所及的一切,都在轻微晃动,像在遭逢一场小型的地震。
看不见脸,声音便成了最直接的表达媒介。
而只是描述事实,在这种情景下,也显得脏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