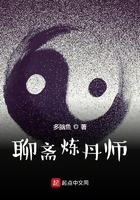小嗨书 > 《再逢秋[破镜重圆]》作者:梨花夜雪 > 第211章(第2页)
第211章(第2页)
只?是一瞬,他已垂下视线。
夕阳洒在男人微颤的睫毛上,又恢复了冰冷。那稍纵即逝的几分眷恋,方宜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渐渐地,郑淮明似乎不再激烈抵抗。
当温热的湿毛巾触上额头,他无力地闭上双眼,任女孩的气息拂面。
他也不再偏头避开方宜纤细手?指间的勺子,只?要是她喂来的粥,都会白着脸吞咽。
方宜以为,郑淮明慢慢接受了她的照顾,是两个人心意逐渐相通的征兆。
然而,一切的发展与她理?解的截然相反。
气切封管后不到一周,郑淮明出现了局部感染的症状,低烧伴随着咳嗽,几乎夜不能寐。可他身体亏空得太厉害,全?靠营养液吊着,承受不住再开创口,只能一边输液消炎,一边慢慢捱着。
咳嗽对于长期平躺的病人最?为难熬,偶尔倚着床坐起来能好受些。但郑淮明总是独自?忍下,从未主动向方宜求助,好几次等她发现,他已经闷咳得脸色惨白、意识模糊,连嘴唇都咬破了。
深夜,方宜交完稿子实在疲惫,不小心趴在桌边睡着了。不知多了多久,睡意朦胧间,又听到细碎的咳嗽声?。
她一个激灵清醒过来,三步并做两步跑到床边。
只?见郑淮明宽阔的肩膀陷在被褥间,整个人艰难辗转,断断续续地呛咳。他一手脱力地揪住衣领拉扯,挣扎间蹭脱了氧气面罩,依旧上不来气,薄唇泛紫,胸膛微弱地颤动着。
一下、一下几近在倒着抽气,可即使已经难受成这?样,他依旧克制着声?音,间或紧紧抿住嘴唇忍耐。
“怎么不叫我?”方宜连忙将病床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