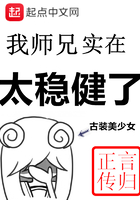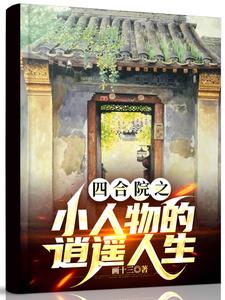小嗨书 > 岐黄手记 > 第362章 辨证论治·寒湿泄泻的判断(第1页)
第362章 辨证论治·寒湿泄泻的判断(第1页)
舌象照片传进苏怀瑾手机时,她刚在笔记本上画完半张病机草图。第一张点开的是城南养老院82岁周老太的——屏幕里的舌头像块泡在冷水里的棉絮,舌苔白腻得几乎看不出舌体本身的淡红色,边缘还印着一圈浅浅的齿痕,像被牙齿轻轻咬过的湿面团。最显眼的是舌面,蒙着层水光,连舌底的络脉都被腻苔遮得模模糊糊。
“这是典型的‘寒湿裹舌’。”苏怀瑾指尖在屏幕上轻点,指腹几乎要触到那片白腻,“苔白为寒,苔腻为湿,齿痕是脾虚的兆头——脾主运化水湿,虚了就兜不住水,湿邪只能往舌头上显。”
陆则衍凑过来看,手里捏着刚打印好的脉象记录,纸页边缘被指腹蹭得起了毛:“老中医说‘濡缓如裹棉’,我刚才查了《中医诊断学》,濡脉主湿证,缓脉主脾虚,合在一起就是‘湿邪困脾’的脉象。”他指尖在“裹棉”两个字下划了道线,“这个比喻很准——按上去软软的,像按在浸了水的棉花上,一点劲都透不进去,跳得还慢,每分钟才54下。”
第二张是4岁男孩小宇的舌象。孩子的舌头小,舌苔没周老太那么厚,却透着股明显的寒气——薄白苔下泛着青,舌尖微微发暗,像被冷水激过。“你看舌尖,”苏怀瑾放大照片,“正常孩子舌尖该是淡红的,他这是寒邪郁在里了。刚才社区医生说,这孩子拉得最厉害时,盖着两床被子还喊冷,手脚摸上去像冰坨子。”
“还有腹痛。”陆则衍翻开病例统计表,指着“腹痛特点”一栏,“60个患者里,57个说‘用热水袋敷着肚子就舒服点’,撤了热水袋就疼得蜷起来——这是‘喜温’,中医里这是寒证的典型表现。”他忽然顿住,指尖在“水样便”“畏寒”“喜温”“舌白腻”“脉濡缓”几个词上圈了圈,“这些串起来,是不是就能定了?”
苏怀瑾没立刻回答,而是点开社区刚发来的症状视频。画面里的周老太正被护工扶着坐起来,说话时声音发虚:“拉的都是清水,一点臭味都没有,就像喝下去的水没经过消化似的……”镜头扫过床边的便盆,里面的排泄物清稀如水,连点粪渣都少见。
“无臭味也是关键。”苏怀瑾关掉视频,语气里的不确定渐渐散了,“如果是湿热泻,大便会臭秽带黏液,肛门还会灼热;但寒湿泻不一样,湿邪重到极点,就成了‘水湿下注’,像没来得及消化就排出去,自然没臭味。”她在笔记本上补了句:“粪便清稀无臭,为寒湿佐证。”
她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伤寒论》,书页翻动时带起淡淡的纸香。指尖落在“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那行,墨字在阳光下泛着柔光:“你看,张仲景早就说过太阴病的特点——拉肚子(自利)、腹痛(时腹自痛),这和现在患者的症状对得上。太阴病的核心是脾胃虚寒,就像炉膛里的火弱了,烧不开水;再遇上连阴雨的‘外湿’,等于往炉膛里泼冷水,火更旺不起来,湿邪自然越积越多。”
她拿起笔,在病机草图上补画箭头,线条清晰得像条引路的河:
“潮湿环境(外湿)→钻进屋里的潮气、墙上的霉斑,从皮肤、口鼻渗进来→
脾胃本虚(内湿基础)→老人脾胃功能衰退,孩子脾胃没长好,本身就兜不住湿→
饮食生冷(诱因)→昨天社区补的饮食记录里,48小时内吃冰西瓜的有32人,喝隔夜井水的28人→
寒湿困脾→外湿、内湿、生冷寒邪凑在一起,把脾胃泡成了冷水里的布→
脾失健运→脾胃像被泡肿的海绵,运不了水湿,也化不了食物→
水湿下注→运化不了的水只能往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