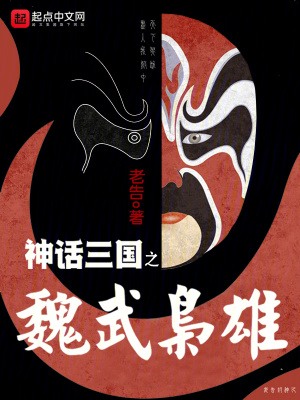小嗨书 > 蠢物 > 第一百三十三章:哥你是不是也被甩了(第3页)
第一百三十三章:哥你是不是也被甩了(第3页)
他面前的实木办公桌干净得如同刚刚被飓风扫荡过。
原本堆积如山、几乎能淹没他大半个桌面的文件、报表、待审项目书,此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几份被处理得井井有条、签好名字归档完毕的文件夹,整齐地码放在桌角。
过去几个小时,萧宥临像个高效指令的机器,以近乎非人的速度和精准度,清空了积压好几天的工作量。
签名的笔迹依旧是他特有的,带着点慵懒劲儿的流畅,只是那笔画深处,力透纸背,几乎要划破纸面。
他下午心情很差。
指尖因为长时间高速书写,指节处泛起一层不自然的白。
手边那杯特助小心翼翼送进来的热美式,早已冷透,表面凝结了一层黯淡的油脂,孤零零地被遗忘在桌角。
萧宥临没有看窗外,也没有看那些处理完的文件。
他只是微微垂着眼,视线落在桌面上。
那里,安静地躺着他的手机。
屏幕是彻底的黑,像一块冰冷的墨玉,映不出任何光亮,也映不出他此刻空洞的眼神。
他就那么定定地看着那片纯粹的黑,仿佛能从里面窥见另一个空洞的世界,时间在空调低沉的嗡鸣声里粘稠地流淌,几乎凝滞。
办公室厚重的双开门被一股蛮力猛地撞开,撞击在侧面的缓冲器上,发出沉闷的一声“砰”。
“哥!我进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