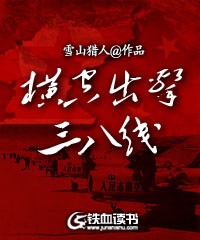小嗨书 > 岐黄手记 > 第359章 年度畅销书·官方的肯定(第1页)
第359章 年度畅销书·官方的肯定(第1页)
仁济堂的诊室里,阳光正透过雕花木窗,在案头的读者来信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苏怀瑾指尖捏着枚银杏叶书签,刚把第237封信放进收纳盒——信封上画着个歪歪扭扭的药罐,是位退休教师寄来的,说按书里的山楂荷叶茶方子调理,血压稳了不少。
手机“叮”地响了一声,是赵小胖发来的截图:国家新闻出版署官网的“年度好书”入选名单里,《岐黄手记》的书名赫然在列,科普类首位的红色标注格外醒目。她刚点开放大,诊室门就被推开,赵小胖举着平板闯进来,额角还带着汗:“瑾姐!中了!咱们书是科普类第一!颁奖词写得绝了!”
平板屏幕上的颁奖词还带着官网的宋体格式,却字字透着温度:“50个病例,既是临床指南,也是文化注脚——作者用中医辨证的细腻(如‘舌苔变化预判体质趋势’)、西医数据的精准(如‘血糖波动曲线验证调理效果’),让古老的中医智慧脱下‘神秘’的外衣,通过现代临床案例,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这是头回有中医书入选。”赵小胖把平板往案头一放,指着评论区里的“恭喜”刷屏,“出版社刚打电话,说编辑群里都在转发,说这比销量破10万还提气——这可是国家层面的认可。”
正说着,门口传来轻叩声。穿制服的年轻姑娘捧着个烫金证书盒,笑着走进来:“苏医生您好,我是新闻出版署的,给您送‘年度好书’证书。”她把盒子放在桌上,指尖在盒面的花纹上轻轻点了点,“我们主任特意嘱咐,一定要当面说句恭喜——评审会上,您这本书的票数是全票通过,有位老评委说‘这才是能传下去的科普,既有根,又有新’。”
苏怀瑾打开证书盒时,指腹触到了丝绒的柔滑。烫金证书上的字迹笔力沉稳,“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红章盖在右下角,方方正正。姑娘又补充道:“评委们说,它最难得的是‘解决了当下的问题’——现代人总说亚健康、慢性病没辙,您这本书告诉大家,老祖宗的智慧里早有答案,关键是怎么用现代人能懂的方式讲清楚。”
把姑娘送出门时,正好撞见祖父在药圃里翻土。老人手里的木锄顿了顿,看着苏怀瑾手里的证书,皱纹里漫开笑意:“我就说嘛,能让人看懂、能用得上的书,总会被看见。”他放下锄头,接过证书翻了翻,忽然转身往堂屋走,“我这就把它挂起来,跟《人民日报》的专访剪报当邻居。”
堂屋的东墙上,早就被祖父布置成了“荣誉角”:最上面是泛黄的“苏氏仁济”老字号牌匾拓片,中间贴着《人民日报》的专访剪报,旁边粘着赵小胖打印的读者打卡截图——有“粥粥”的舌苔对比图,有宝妈儿子的“草莓舌”好转照。现在祖父踩着竹凳,把烫金证书用红绳系在正中央,正好在剪报和截图中间,像给这面墙定了个暖烘烘的调子。
“这样进来抓药的老伙计都能看见。”祖父拍了拍证书边角,忽然朝门口喊,“老王,你来看!”正在门口等抓药的老王凑过来,看着证书笑:“早就说瑾姐的方子靠谱,现在国家都认了!我那孙子在上海读大学,我上周刚给他寄了本,让他照着调理失眠,比我天天打电话催管用。”
下午赵小胖带着广告公司的人来,要把颁奖词做成海报。他指挥着工人在中心走廊贴背景板,自己蹲在地上摆读者打卡照片:“左边放‘痰湿组’的粥粥,右边放宝妈的‘草莓舌’,中间留块空贴颁奖词,保证路过的人都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