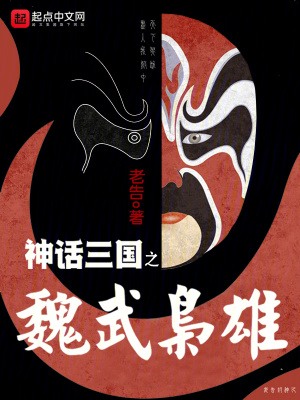小嗨书 > 蠢物 > 第一百三十三章:哥你是不是也被甩了(第1页)
第一百三十三章:哥你是不是也被甩了(第1页)
“裴肆。”
姜余的声音响起,出乎意料地平静,没有一丝波澜,像结了冰的湖面,清晰地回荡在过分安静的单间里,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分量砸下去。
“你不是很在乎她么?你为什么现在看她……就像个陌生人。”
裴肆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似乎没明白姜余突如其来的平静意味着什么。
她的目光越过他僵硬的肩膀,落在窗边那个依旧安静坐着的单薄身影上。
沉音夕微微低着头,视线似乎又回到了自己并拢的膝盖上,仿佛刚才那句石破天惊的问询从未发生过。
只有她放在膝头的手指,无意识地、极其轻微地捻着病号服粗糙的布料。
“我……为我自己的未来悲哀。”
姜余清晰地,一字一顿地继续说下去,目光重新落回顾言深骤然变得难看至极的脸上。
悲伤吧,悲伤吧,真疯子也需要点情绪价值去遮掩他的卑鄙。
姜余的声音停顿了,再抬眼,脸上就是一捧清泪短线似的滴答,半含生理恐惧,半含假装。
她很少哭,也很少跟裴肆示弱。
她大多时候有种强悍的野性,锋利到让人无法驯服。
裴肆知道姜余不喜欢他,所以她的眼泪,大多是欢愉时情动的生理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