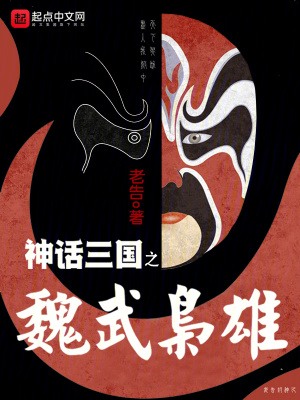小嗨书 > [废文 更44]桃溪村记事(1v1)作者:秦柒 > 第25章(第4页)
第25章(第4页)
一分钟后,陶知秋眼睛瞪得像铜铃,蔫哒哒地打开门又去找谢淮之,他大概也觉得这样很烦人,声音小得像蚊子一样不好意思地道:“淮之哥,我还是睡不着。”
谢淮之倒也不恼,将他领进来还是安置在刚刚的大椅子上,陶知秋屁股往上一挨,脑袋就开始小鸡啄米似的点,谢淮之放下铅笔,白纸上勾勒出的哪里还是什么花圃和院子,分明是陶知秋的身形。
“知秋,”谢淮之压低声音唤他,“坐着睡不舒服,去床上睡吧。”
总归他今晚不打算再睡,就留陶知秋在这睡一晚也无所谓了,否则再折腾几回,天都要亮了。
陶知秋沾床就睡熟了,也不知道什么习惯,天气这么热还是喜欢裹被子,谢淮之将放在他屋子里的电扇拿过来开到一档,慢悠悠地吹着。
人是睡着了,但梦却不消停,或许是今晚提到了某个话题,又或许是白日里关于说媒的事情让他耿耿于怀,陶知秋梦里都是谢淮之。
梦见小时候的谢淮之在镇上打零工挣钱,又梦见长大后的谢淮之独自一人背着行囊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去上学,画面最后定格的瞬间,却是他抱着谢淮之,哭得抽抽搭搭说不许他走。
隔着一层雾气,梦里的陶知秋不停地眨眼想要看清楚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是穿着西装戴着新郎胸花的谢淮之,朝他笑着挥手。
再睁眼时,天光大亮。
谢淮之已经不在屋里了。
陶知秋默默地将身子又往被子里塞了些,他知道梦都是没有逻辑的,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没印象的画面,可是偏偏最后那一幕又让他觉得奇怪,他隐约察觉到什么,又微妙地不愿细想,蒙着脑袋当鸵鸟,后知后觉这是谢淮之的被子,又跟屁股着火似的一脚踢开了。